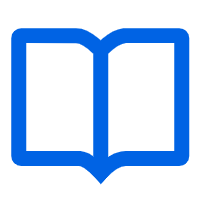西安五行属什么?
东西南北中也即金木水火土,中国道家称为“五行”,其“五方”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亦有重要影响,如“天下”的概念就是以国都为中心,周围五百里的区域为“郊”,从“郊”外到另外的“五方”又各有五百里,称为“甸服”,再外则分别称为“侯服”和“绥服”,“绥服”之外“五方”才是所谓“天下”。
那么古代中国“天下”的中心在何处呢?根据《周礼·考工记》的记载,“匠人营国,方九里,旁三门,国中九经九纬,经涂九轨,左祖右社,面朝后市,市朝一夫。”
这一文献记载的是周王朝国都营建的基本规划原则,即方正的都城之中南向正门为王的“祖庙”所在,左侧应属“社稷”;都城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是“中央朝堂”和“集市”。
这表明中国古代王朝的首都和“宗庙”、“社稷”(土地之神)以及“中央王朝”的实际统治区域具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。
秦朝统一和“汉承秦制”,中国的首都建置在“天下”的中央——“长安”,《诗经.小雅.正月》有“谓天盖高,不敢不局;谓地盖厚,不敢不蹐”的说法,这是说天高地厚而不敢不卑躬屈膝。
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,“天”为宇宙空间和“天象”,“不敢不局”的“局”本写作“倨”,即是两足叉开或仰卧的意思,这表明“天”在人站立时,只要“仰首”便可看到和观察到,换言之,这一诗句中的“天”并非遥远的太空或宇宙,而是可以“仰首”观察的“天象”,至于“地”,人站立时只有“足踏其上”,要“视之”则必须曲身俯视,因此“地”本写作“地”,所以人们对地“不敢不局”也不“彳”,而是“屐”,必须行走或迁移,即“屐履而视之,亦不可不”小心从事,这也表明此处“地”的外延不可能如“天”那样大得惊人,它实际上指的只是人们“足踏”和“屐履”迁移的区域,它实际的外延应只局限于人活动的区域,亦即“天下”的范围,此诗产生于周朝。
那么,周朝的“天下”是什么概念呢?据《史记.吴起列传》记载,吴起对魏武侯说,“(魏国的)西河之外王庭数千里”,如果北至赵国从安邑县(今山西夏县西北)起,南至楚国从宜阳县(今河南宜阳县西)起向南、北各量1500里(450华里),西河之外的“王庭”约达17万平方公里,大致包括今陕西、河南、山西接壤地区。
从《诗经.正月》的产生之地“召南”(今陕西和晋南)和“王庭数千里”的西河外,可以知道“不敢不局”的“局”和“不敢不屐”的“履”所指的“天下”就是指方圆数千里之内的渭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。
从汉代文献的记述中可以看出,这一“天下”概念并没有多大改变,如《史记.日者列传》记有“日者之传……避诸凶忌,归之于无疵”。
据《后汉书,郡国志》可知,《日者列传》所记“方诸”包括“方诸”和“方与”。前者属吴郡(治所在今江苏吴县东南),后者属山阳郡(治所在今山东金乡西北),二者相距在1200里以内,这一“天下”的外延与《诗经》中的基本一致。
“天下”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推移不断扩大,但无论怎样扩大,“天下”的中心始终在“天下”的中心——“两京”。
在东汉以后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,“天下”无疑在继续扩大,但“京师”,也就是“天帝和祖先之灵”之所佑的“大汉皇朝”的核心地区并没有多大的改变,“京畿”之外为“司隶校尉”所辖的“天下”中央地区,再外才为“州郡”。
因此,无论怎么扩大天下,在人们心目中最重要、最神圣的还是帝国的“大梁”——“